多年老友在离城不远的村子里租了两孔破旧的老窑洞,快改造好的时候才告诉了我,对她的这种躲进村落瞎折腾,我早已习惯。她的上一个村居窑洞租了也有几年时间,离城相对远一点,我去过两三回,院子坐北朝南,改造的相对简单,院子很大很大,种了一片的瓜果蔬菜,坐在院子里抬头就是一个土丘,丘上杂树丛生,丘底青石裸露,野趣十足,她没事就出城向西钻沟而入,待在自己营造的一方小世界里,羡煞旁人。
新窑租定后,她对石窑的内部进行了功能性改造,增加了卫生间和浴缸,改造了水电管路,铺设了地板,更换了新的门窗,粉刷了内部的墙壁。石窑的外边重新做了雨搭,粉刷了外屋面,院子里也进行了收拾,新建了两间坐南朝北的小房子,一间是厨房,一间是杂物间,南北屋之间的小院子里砌了一个不算大的长条形鱼池,放满水养了几条锦鲤,还沿着院墙给鱼池上装了一个小的瀑布式喷泉,院子里留出一点细长的绿化地块,栽植了点长寿菊,经过长达几个月的断断续续改造,小院迎来了它的新生,老友也又有了一个休憩和发呆的地方。
小院坐北朝南,是陕北人说的“人”字窑,两孔窑洞共用的窑腿中间开了一个仅能通人的小窑口,一孔会客,一孔居住,日头从早上能晒到下午,既保暖又采光,时间把日子拉长,太阳把日子充满,人箍窑,窑护人,人生人,窑养人。窑洞的北面是一座不算太高的山坡,坡上还住着几户人家,坡内有一条深沟,从西北到东南方向延伸到门前的麻家塔沟内。窑前面是一片沿麻家塔沟道的耕地,这片耕地能够用自流水灌溉,就是陕北人说起就自豪和羡慕的水浇地,土壤肥沃,大大小小的被分割成多块,种植各种农作物,宜居又宜耕,风水宝地。
今年年中,老友问我种不种地,她在村子里租了一块地,种不了那么多,还剩下有两分大小的地,要种就自己进去收拾一下,我自小就和土地打交道,对土地有着割舍不了的感情,哪能让地闲着,和母亲钻沟而入,找到地块后拔草、平整,回老城里买了玉米种子,当天就种下了。种下的第二天,老天赏饭吃,下了半天的雨,中间我和母亲又去锄了两回地,现在玉米已经长出了樱子,吃到嘴里指日可待。有两回是我自己去的,从地里出来顺着同村的水泥路,不需要刻意去找,凭着多年神交的直觉,我很自然的就找到了老友正在改造的小院,院门大敞着,进去之后稍显凌乱,我坐在窑洞里的摇椅上,看着日光从未安装门窗的窑口射入,时光慵懒,就一个人静静的坐着,等待着日头慢慢的移动,想着改造完成后的样子,日子应该是会很惬意。
小院终于在初秋收拾妥当,老友文艺老青年的劲一下就上来了,试探性的让我给小院取一个名字,我这岂不是贪天之功,从租到装,我寸力未尽,到收获果实的时候,画龙点睛要我来,抹不开面子,想着前两次自己一个人待着的场景,在乱中取静,于繁中化简,老友一人一院,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心灵居所,不是世界上最诗意的事情吗?也是我们多少人向往而求之不得的事,取“无二居”,也算贴切应景。
老友拉了一个群,把相知多年的密友、朋友约到一起,喝个下午茶,吃顿柴火饭,一来是为了暖暖房,聚拢下人气,二来也是想让她的朋友们相互认识一下。当天下午,她和另外两位女士先到,收拾房子,准备器具,切配食材,等我们陆续到的时候,肉已经炖在了院里支起的锅里,炉子里火红的木炭散发着炽热,迎接着主人的朋友们。院子里人一多,显得就有点小了,人与人的距离一下子就被拉近了,大家挨个介绍着自己,一瓶饮料、一瓶水也能喝出烈酒的味道,有一搭没一搭的聊着天,时光流逝,羊肉上桌,饕餮而食。
日头西下,隔壁破旧窑洞前一棵桃树在微风中摇曳,树头有一半已经干枯,如同快乐的日子般过半,下半程开始。水足饭饱,儿子把羊肉咥饱就想回家,我内心里是想着留下来,享受下放松的时光,奈何子命难违,向老友简单告别后就驱车离开了。回到家后,孩子在小区院子里疯耍,我沿着小区绕圈圈,一圈又一圈,生活为啥团团转?皆因绳未断,我的那根绳拴在了哪儿?我的几根绳过往拴在了不同的人身上,缠绕纠结,自己未曾理出过哪怕一点点头绪。
当晚,微信群里发出了大家饭后唱歌的视频,有歌有友,生活乱就乱吧,至少那一晚大家是开心的。
我们都曾经有那么一刻也想成为某一个人的唯一,愿老友在无二的居所里成为那个唯一。
无二居,理想的居所。无二,理想的世界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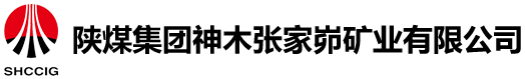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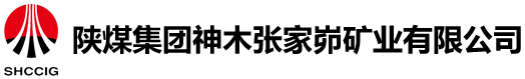



 发布日期:2023-11-13
发布日期:2023-11-13
 点击量:1527 作者:刘波 来源:
点击量:1527 作者:刘波 来源: