街口的风又硬了几分,直往人领口里钻,像把钝钝的刀子。这风的凛冽里,却挟来一丝熟悉的、霸道而温暖的香气——是腊味。不是一缕,而是混着柏枝的青涩、松针的微辛,还有一种厚墩墩的、油脂被时光驯服后的醇厚肉香。这香,像一只无形而柔软的手,一下子就把人攫住了,径直拖回到那些被烟熏火燎得暖黄的记忆里去。
那是老屋的堂屋,高高的房梁下,黑黝黝地悬着一条条、一串串的年货。腊肉是主将,肥膘已然透明,如凝脂,透着一层蜜蜡似的温润光泽;瘦肉则被岁月风干,沉淀成深沉而踏实的绛红,像冬日黄昏最沉静的那一抹霞。底下是腊肠,红白相间的纹路,被肠衣妥帖地包裹着,丰腴而圆满,静静等着灶火的唤醒。这些东西,日日悬在头顶,从腊月初始,便成了生活的一部分。你从下面走过,一抬头,望见的不是口腹之欲,而是一份“家有余粮”的笃定,一种被富足与期盼静静笼罩的安稳。
这安稳,是烟火一寸一寸熏出来的。入了腊月,母亲便选了上好的柏枝、花生壳,还有晒干的橘皮,在屋角那只废弃的破铁锅里,燃起一蓬不起明火的烟。那烟是活的,先是青白地、试探性地升起,渐渐便成了沉稳的、蓝灰色的绸带,袅袅地,绵绵不绝地,缠绕上那些生肉。母亲常搬个小凳,坐在不远处,手里纳着鞋底,偶尔轻声咳两下。那烟味是呛人的,带着植物燃烧后微苦的芬芳,丝丝缕缕,钻进肉的每一条肌理。我那时总觉得这过程太慢,不耐烦。母亲却说:“急什么,日子就是要慢慢过,味道才进得去。”她望着烟雾的眼神,是出奇的静,仿佛在守护一个古老的、与时间有关的秘密。现在想来,那秘密大约就是“熬”与“等”两个字。好日子,好味道,都是光阴文火慢炖的赏赐。
等待的尽头,是除夕的团圆。那条最丰腴的腊肉被郑重取下,在温水里洗去浮尘,露出本真的面貌。上锅蒸了,水汽沸腾起来,那被封锁了一冬的浓香,便像决了堤的洪水,汹汹涌涌地漫出来,侵占屋子的每个角落。端上桌时,肉片切得薄而大,灯光下,肥处晶莹如琥珀,瘦处绯红似珊瑚,错落有致地铺在青瓷碗里。第一口,总是给最年长的祖父。他眯着眼,细细地嚼,并不说话,只是喉结满足地动一下,深深浅浅的皱纹里,便漾开一层无声的笑意。于是我们也动筷,那味道便在舌尖炸开:咸香是骨架,稳稳地托着一切;烟熏的况味是魂,有一种山野与炉火的深邃;而后,才是猪肉本身的丰腴甘美,一丝一丝,在热气里融化,熨帖到肠胃的最深处。一年的奔波、分离、种种不易,仿佛都被这口厚实而踏实的肉,温柔地抚平了。
此刻,我站在这异乡的风里,贪婪地呼吸着这熟悉的香气。楼宇的缝隙间,天色已近黄昏。我忽然觉得,年味儿或许从来不是什么虚无缥缈的喜庆。它就藏在这腊味的烟与咸里,藏在母亲被熏出的咳嗽里,藏在祖父咀嚼时无声的皱纹里。那是用最朴素的食材,对抗时间,沉淀风霜,最终熬出的一碗“稳当”。这稳当,足以让每一个漂泊的胃与心,在岁末的寒风中,找到那座可以回得去的、灯火通明的堂屋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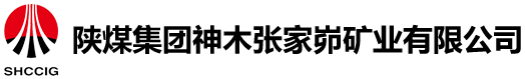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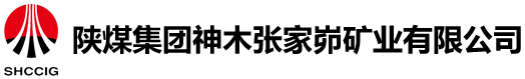



 发布日期:2026-02-13
发布日期:2026-02-13
 点击量:8 作者:刘欢 来源:
点击量:8 作者:刘欢 来源: