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妈妈,你知道吗?月亮还叫玉盘。”
晚饭后,女儿突然冒出这么一句。她刚满四岁,上幼儿园中班,说话时眼睛亮晶晶的,像在说一个非常神秘的话题。我顺着她肉乎乎的小手指向天空,那轮月亮确实圆润、光洁,温润地浸在深蓝天幕里,边缘微微泛着青光,真像一块被时光打磨得极好的玉。
“是李老师教的。”她得意地补充,小脑袋仰得高高的,小脸上满是“我知道一个了不起的词”的骄傲。
我忽然有些恍惚。“玉盘”这个词,从她稚嫩的嗓音里流淌出来,竟如此新鲜又古老。让我想到那首诗,“小时不识月,呼作白玉盘”,但那时朗朗上口的是音节,并不是真懂何为“玉”,更不解那清辉万里背后,一代代人凝望的、共同的乡愁。
而她呢?她的小脑袋瓜里,“玉盘”大概就是个新学会的、好听的词,和“滑梯”“彩虹糖”并列,是她探索这个世界的又一块小拼图。她还不明白,这个词承载了千年月光。
这让我想起她第一次对“中秋”有概念,是去年。
那时她三岁多,我们指着天上越来越圆的月亮,告诉她:“快中秋节啦,可以吃月饼,看月亮。”她似懂非懂,也许只记住了“月饼”是甜甜的、圆圆的点心。今年,她到底大了一些。幼儿园里做了灯笼,读了绘本,讲了嫦娥奔月的故事,还用彩笔涂了可爱的玉兔,那些古老的故事,就这么借着颜料和纸张,悄悄印在了她心里。
这或许就是节日的意义,它像一条隐秘的河流,我们带着下一代涉水而过,将古老的传说、共同的记忆,以及那份对团圆的朴素信仰,小心翼翼地渡给他们。
看着她专注望月的侧脸,我忽然意识到,我正亲眼见证着文化最初的模样,是如何在一个纯净的生命里扎根的。它不是课本上需要背诵的诗句,也不是仪式里必须遵守的规矩,而就是这样一个寻常的夜晚,一个新鲜的词语,一份对遥远故事的好奇,和一种想要与月亮分享甜食的天然亲近。
我们这代人总感慨年味淡了、节味变了,仿佛那些热闹的仪式一散,传统就跟着淡了。可此刻看着女儿,我忽然懂了:节日从未真正改变,它只是换了一种更质朴的方式,在下一代身上悄然延续。它藏在孩子学会的一个新词里,藏在她对古老传说的一丝共情里,更藏在她依旧愿意仰头看月亮的那份专注里。
是啊,无论时代如何翻涌,科技如何狂奔,只要某个秋天的夜晚,依然有孩子指着天空说“月亮像玉盘”,只要那份仰望星空的初心不曾泯灭,那轮照过李白、照过苏轼,照过无数代人团圆与别离的月亮,就永远年轻,永远温润如玉。
原来中秋的圆满,从来不止于此刻家人围坐的温暖。更在于我们确信,这缕皎洁的月光,会带着“玉盘”的故事、嫦娥的传说、团圆的期盼,这样温柔地、稳稳地,一代一代照拂下去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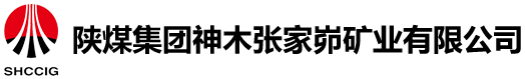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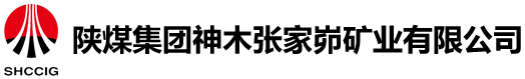



 发布日期:2025-10-03
发布日期:2025-10-03
 点击量:791 作者:贾艳 来源:
点击量:791 作者:贾艳 来源: